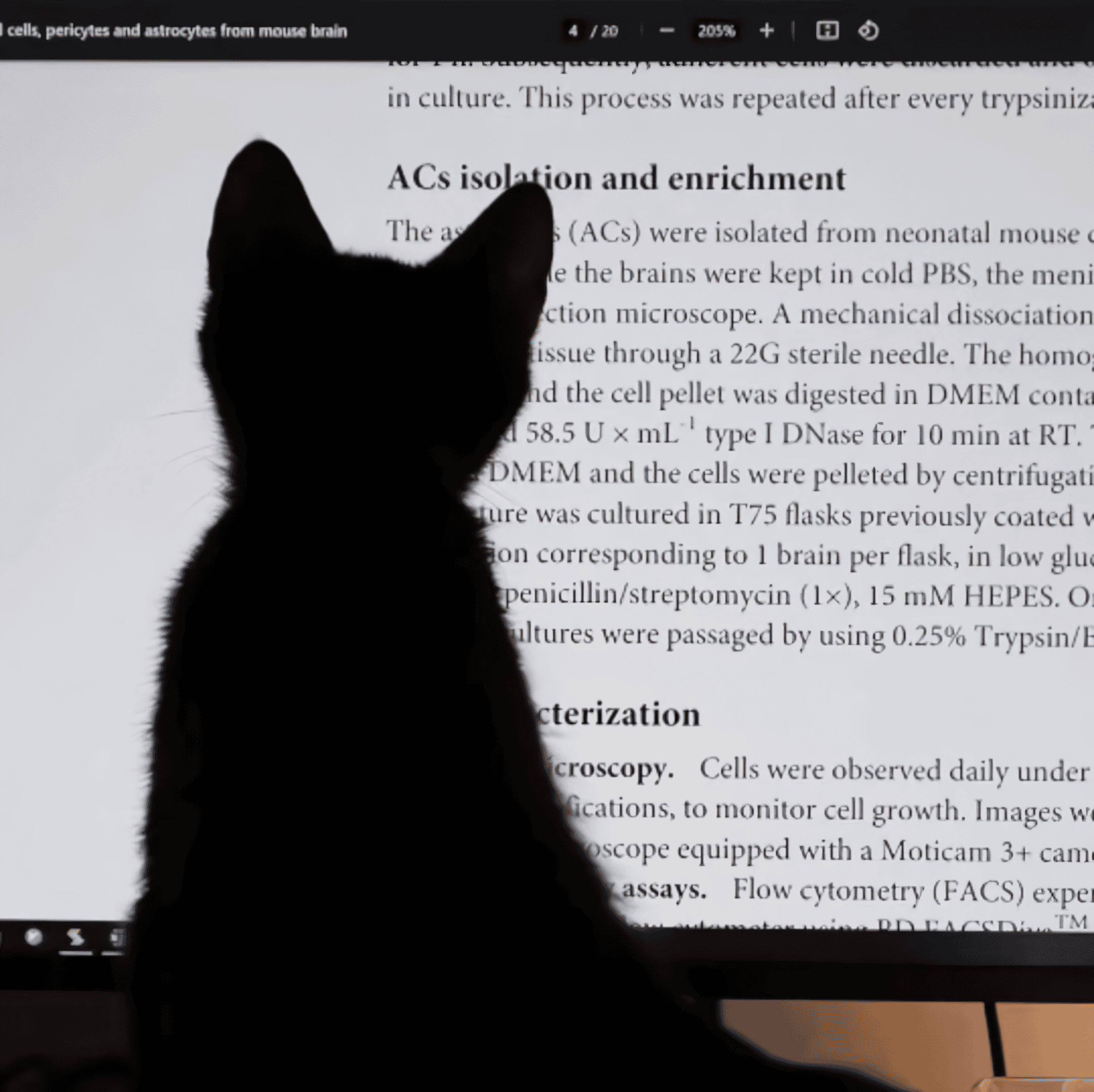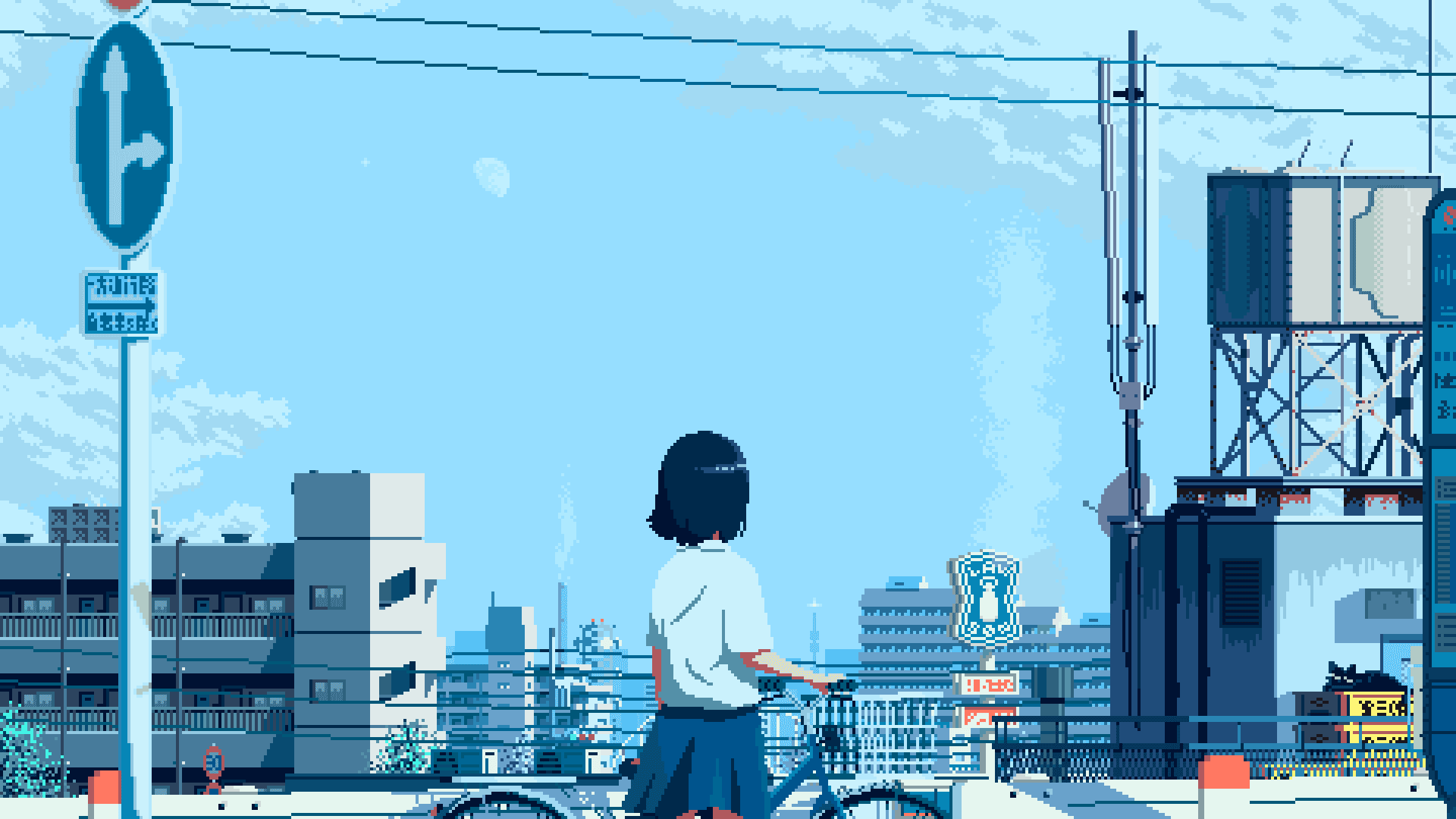不明物体
“它死了吗?”
这个消息如同霹雳,瞬间将沉寂的场所激活。目光纷纷转向言辞的中心——A 伸手指向侧面。
“就在那个壁龛旁!”A 惊呼。
目光顺着 A 的胳膊流了过去。
“它不动了。”
“不对啊,它明明还在抽动!”
“那是呼吸的起伏。”
“这…… 这这分明…… 只是一堆酒瓶。是谁刚刚往上…… 丢了个空瓶…… 塌了!”
“酒蒙子!”
“哈哈哈哈哈哈。”众人欢笑。
“这是一堆还没开盖的酒呢,你快过去捡一瓶喝。”
“你敢去吗?”
“快去快去。”
“去啊,快啊,不去我踹你了。”
“我才…… 不去。”
众人又是一顿欢笑。
“它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!”一阵惊呼,伴随着一阵痛苦的哀嚎。
“我的天,你们是怎么敢笑得出声的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?它就在那儿,就在壁龛旁边。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哪儿的,也许是我们还没进来的时候就一直在这里吧!但是你们,你们居然,没一个人发现它!它那么大那么明显,那么恐怖!它就在那儿!它就在那儿…..”
“叽里咕噜的,有本事你去看,你凑到它旁边去。凑到它旁边去探探它的气息。如果它还有气息的话…… 哦对了,你是不敢吧?你敢吗?说话!”
一阵沉默后不知是谁噗嗤一声笑了
“懦夫,coward。嘴皮子动地比脑子快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,你根本没有一点胆量去探探它。且不说探,你能往它的方向多走一步路我都要尊你为勇夫。你这个废物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的勾当。旁边的那个人,以前被人堵巷子里了,你就在旁边看着,不报警就先不说了,你就在那儿呆愣着看。那个人逮住间隙火速跑出来了,恶人追到路口,看到你,你当时又做了什么呢?你这个怂货,怕自己落得那个下场你就给人家逃跑的方向供出来了。事后还恬不知耻说自己迫不得已。在座的各位谁信他的荒谬言论?谁信他的圣洁名声?”
沉默一阵后,迸发一阵哄笑。
“真是不如以前了,觉昨是而今非。如果你要处在某一个位置——在此正如戈夫曼的形象整饰一般——在整饰的过程,与他者的关系本应该是互促的。自我展演对他者来说是利他的,但是渐渐的自我却深陷泥沼,整饰的持续导致自我成为了整饰的表现形式,自我已经和整饰行为绑定在了一起。整饰原初的目的早已湮灭,而自我依照剧本发生行为的只是因为某种惯性,是不得已,是彻底的束缚。那么目的消失在哪儿了呢?如果共同整饰的他者能够指认自我的展演,能够指认自我的展演内涵的利他属性,同时对自我的展演进行回应,甚至开展自己的展演来配合。那么这个目的可能仍然能够清晰吧?要知道曾经目的是明晰的,而整饰的他者也会共舞。如果让这一切的整饰延续,会不会是……?
“你们快听啊,这个沉思者、君子、超脱者、哲学家和神学家又开始布道了。什么‘整布’?什么‘他着’?什么‘湮灭’?敢问这位贤者这些都是什么意思?所谓的展演共舞都是什么意思?这些话和那位圣洁人士有关系吗?”
“连你也是这样…… 为什么要要求所有人都和你保持同一意志呢?遵从你会让你感到开心,稍微和你的意见有点出入,你就要开始大肆镇压。你无法接受别人的观点,因为这个世界是围绕你旋转的,世界的程序也都是应你的要求来决定的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有很多套秩序并行的吗?你不会还天真地觉得种种事件都是只有一套规则在发挥作用吧?规则间难道都是不可兼容的吗,它们就必须非此即彼而毫无中间地带?仿佛种种问题种种世界都有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标准答案。除了标答绝无他者。”
“你说什么呢,神学家。我只是问问你刚刚在嘀咕什么,你这样攻击我是什么意思?既然你这么会说,你这么聪明,你用语天花乱坠让人难会其意,不如你动用你那个充满哲思的脑子思考一下,回答一下懦夫的问题——壁龛那儿的东西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吧!”
“他不说话了,哈哈哈哈。”
“哈哈哈….”
“你不是很聪明吗?你不是很会说吗?怎么现在哑口无言了,神学家。哦不对,神棍!”
“哈哈哈哈神棍”
“对啊他就是个神棍罢了”
“神棍!只会批判别人的神棍!现在到了检验的时间了。你标榜理性,标榜交往理性,借由理性攻讦别人。你说别人强加观点,那你刚刚自己批判别人的观点,又何尝不是一种将自己不要强加于人的观点强加于人?你和他难道不是一路货色吗?让我来说说你们的不同吧——那就是前提!你们唯一的不同就是前提不同,你是所谓的理性,这个理性仍然值得推敲,因为它是服务于你的思维范式的,而他只是抛弃了这个壳子。你们本就一路货色。你看你脸都绿了,比壁龛下的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还要绿!你不是理性人吗?现在感性上头了,拳头攥紧了,理性说服不了就要感性压制了对吗。那我还说错了,你比他还要恶劣,你追求的是肉体的消灭是吧。我说的没错吧?神棍。都不能叫你神棍了,应该叫你束棍!”
一只空酒瓶在空中飞翔。
“不许你侮辱理性!”
神学家脸涨得发绿,恶气大喘。还好酒馆人满为患,神学家和攻讦者中间有一道厚厚的人墙,不然现在你来我往的就不只是言辞了。
又一只酒瓶在空中飞翔。
“不许你侮辱我!”
最初攻击懦夫的人脸涨得发红,粗气大喘,仿佛刚从冰窖里爬回来。好在攻讦者选址不错,在酒馆正中间,像帝企鹅幼崽一样被簇拥在人群的最中央,离他们俩都还挺远,免去了皮肉之苦。
又一只酒瓶飞翔在空中。也许我们看到的是本世纪最为激烈的酒瓶空战吧。
“忍你很久了闸总!”
可能是酒壮怂人胆,也有可能是发现了自己的同伴,懦夫突然一改常态,展现出了性格里最为坚毅、最为决绝、最具攻击性的一面。小小的酒馆瞬间化作了四股势力,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!
一只白猫似乎听到了馆里喧闹动静。它刚睡醒,它自然是不能够明白在不远的前方,那一团蠕动的密集身影为何聚集、为何蠕动。它看着原本端坐桌上的绿色酒瓶在天上飞来飞去,迷惑着伸了伸懒腰。
从壁龛上跳下,绿光剥离,洁白的毛重回它的身上。